-
赵刚论《夜行货车》:战斗与导引
关键字: 台湾文学陈映真夜行货车陈映真台独台湾龙应台这是头一次陈映真在小说创作中表达了他对中国大陆“走资”的焦虑,以及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的终归徒劳的大恐缦缦。这是1982年底的小说。至于1977- 78年陈映真写作《夜行货车》之际,这样的一种对“走资”的焦虑是否已经浮现,我缺乏足够的论断基础,但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崩落的恐惧,则已经很清晰地出现了,虽然恐惧的原因与“改革开放”可能无关,而是对于文革后期越来越多的暴力,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群体所展现的人身暴力与人格扭曲的震惊。陈映真在1979年底,在《夜行货车》小说集的《序》里,虽然表达了他对中国的文学家、知识分子和“全中国人民”的不熄的信念,但也明确表达了他的高度受挫与惊骇。他说:
“在中国,和在古老的亚洲一样,一切不屑于充当本国和外国权贵之俳优妾妓的作家的命运,是和写一切渴望国家独立、民族的自由、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和公平、进步的人民一样,注定要在侮辱、逮捕、酷刑、监禁和死亡中渡过苦艰的一生。近百年来,在中国,有许多作家曾以孤单的身影,面对从不知以暴力为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做过勇敢而坚毅的抗争;也为曾信其必至的幸福和光明,歌唱过美好而充满应许的歌曲。然而,曾几何时,他们也以更其孤单的身影,在腐化和堕落的革命中,或破身亡家、或备尝更其残酷、更其无耻的损害和侮辱。”(35)
如前所论,《夜行货车》表现了多重焦虑,但其中最大的焦虑,毕竟还是“中国”。对展现了一种强烈的第三世界敏锐感觉而相对回避了“中国”的“华盛顿大楼”系列的理解,必须要考虑到作者此时的深度困惑。
相对于1959第一篇小说《面摊》以来那一直不断的“橙红的早星”的参照,以及《山路》对革命理想的痛苦追寻,此时的陈映真不知如何诉说中国,而客观上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他只得论列“第三世界”。这么说来,陈映真的小说,比起陈映真的论文(好比《“乡土文学”的盲点》)来得“更真实”,更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非理论意识层次的精神困境──他在论文中毕竟还是可以比较无碍地写“民族文学的立场”,以及民族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的互参性……。
今天看来,由于《夜行货车》对“中国”的失语,以及在这个条件下对独派的“导引”企图,使得这篇小说还是不期然地但似又理所当然地落在独派的一厢情愿的喜闻乐见──尽管,陈映真苦心孤诣地丢出“新殖民地”、“南方”或“第三世界”等议题;尽管,陈映真那么费尽心思地塑造了“詹奕宏”这样的主人公;尽管,陈映真似乎是用“景泰蓝的戒指”让男女主人公对“中国”有所盟誓。
但平心而论,“误读”的责任固然不都在独派读者身上,但实在也难以说就在小说作者身上,因为陈映真对“中国”的暂时失语,反映的是陈映真所难以逃避的因历史条件而形成的精神危机。《夜行货车》于是现身说法了一个危险教训,那就是,如果无法在思想上面对“中国”这个与台湾社会经纬交错勾连万端的巨大现实,也就意味着这个思想是没有出路的,而且会陷到轻易为对反力量所整编的后果。
以台湾为一种在地实践的空间尺度,以阶级政治替代族群政治,甚或从第三世界立场论述一种左翼理想主义……,这些想法本身诚然良善,但如果它们无法替代对“中国”的思考,那么,以它们为基础、为理由取消“中国”议程,则可能会转变成一种迂回的逃避。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反省我自己以及我长期所属的一个刊物《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由于一种洋左的知识与政治立场,无能把自己的议题与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近现当代重要议题结合起来,反而习惯性地以洋左的进步语汇(包括批判、公共、反全球化、多元主义、基进民主…..)“介入”台湾现实,结果是不但因为不接地气而无介入之效,反而,更不期然地,在社会急遽变化时期,为反动力量拿来当做他们的概念武器。(36)没有理由相信“第三世界”、“去殖民”等“进步”概念在避免这样的收编时,一定占据任何优位。没有“中国”,第三世界站上去也会踩空的。
然而,话说回来,在这篇小说里,陈映真是否又真的完全无法论述“中国”呢?并不是的。他是困惑于不知如何正面论述中国,但这不表示他也不知道何种关于“中国”的理解是错的。于是,我们最后来讨论一下这篇小说比较难理解的一个有关“沙漠”的隐喻。
女主人公刘小玲十多年来不断梦到一片“寂静的、白色的、无边的沙的世界”,其中没有一切生命(好比仙人掌)或生命的遗迹((好比“野牛的头骷髅”)。
最初,这片沙漠使她骇怕,把她从梦中惊醒,但后来因为常常做这个梦,习以为常了,就敢于在梦中注视它,从而竟然对实体沙漠感到兴味。当晚宴的贵宾达斯曼先生,以其业余生态学研究者的善意,告诉刘小玲沙漠其实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时,刘小玲想表达她的不同感受,但小说并没有让刘小玲完成以“But”开头试图表达不同感受的句子。但我们理解,刘小玲并非要挑战达斯曼先生关于沙漠的科学知识,而是要说,那样一个事实上充满生机的沙漠,可以是很多夜行动物的故乡的沙漠,并不是她在长年的梦境里所感受的沙漠。
沙漠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指向了刘小玲的某种深层的难以言说的恐惧、焦虑或虚空。那么,这个从她中学生以来就纠缠不已的梦境到底要如何解释呢?我以为,“沙漠”是陈映真用来描述作为流亡群体的外省人精神深处的一个最恐惧的状态──一种没有故乡的、失去源头活水的,所有为之灌注下去的水都将快速消失的深度枯竭状态。那么,如何理解刘小玲,作为一个所谓的外省第二代,为何还长期做着“沙漠”的噩梦呢?
要理解这个梦,就必需找到历史切入点:两岸分断与国共内战。
如果说,理解詹奕宏何以是一个如他那般的愤青,非得从他的家庭,他的成长背景,特别是他的父亲处着手,才能寻得解答,那么刘小玲的“祕密”也得从同一路径寻觅。当小说费解地指出刘小玲自从青春期以来就受困于一种如此之噩梦时,我们别无其他线索(事实上,作者也刻意封起其他线索的门窗),只能从刘父那儿获得些许解释路径,特别是小说已经告诉我们刘小玲是在颓唐自弃的老父,与背叛遗弃老父的年轻母亲之间,选择了认同父亲。(37)那么,如果刘小玲认同父亲,那么他父亲不是还有“中国文化”吗?为何她还是做着这样的噩梦呢?
刘父曾是一个“活跃在民国三十年代的华北的过气政客”,人称“刘局长”,根据随着来台的老家人周妈报导,刘局年轻时“一次枪毙十个把人,眼皮都不霎一下”。但来到台湾以后,诸事不问,不修边幅,完全变成一个散人,而在年轻他三十岁且因经商成功而越来越强悍的少妻眼中,则完全成为了一个“脏老头”,一个“破旧的、多余的人”。对于妻子曾对他东山再起的鼓励,他报以“二十岁我从日本学兵回来,什么我没抓过,什么我没见过?”。这样一个刘局,对于妻子的冷落、揶揄乃至背叛,似乎毫不上心,终日一袭长衫,“时而弄弄老庄,时而写写字,又时而练练拳,写一些易经和针学的关系之类的文章,在同乡会的刊物上发表。”
- 原标题:赵刚论《夜行货车》:战斗与导引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李泠
-
● 观察者头条 ●风闻 · 24小时最热 查看全部>>最新视频最新闻 Hot
-

这个时候德防长还要捧美踩中俄 美主持人都听不下去了
-

你往哪儿瞅?
-

麻疹免疫率跟非洲一样!意民粹助长疯狂反疫苗运动
-

全球200多处机密坐标外泄,美英法俄都被它坑了!
-

美媒鼓吹慈禧是中国女权先锋,为了啥?
-

北约峰会刚开始 特朗普就先批了德国:你们就是俄国人的俘虏
-

“尼加拉瓜之春”持续85天已超300人死 学生领袖很感慨
-

漂移压哨绝杀!你正在收看幼儿园篮球全国大赛
-

讨薪!25年御用司机和特朗普反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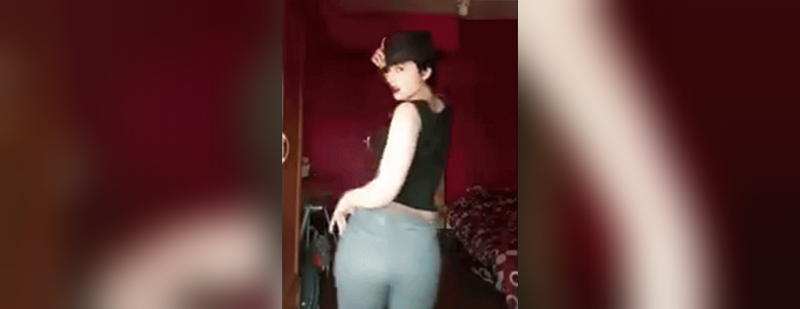
伊朗网红上传跳舞视频被捕,姑娘们“反了”
-

“纽约时报fake news!美国强烈支持母乳喂养”
-

“当前形势下,德方愿同中方开展‘工业4.0’合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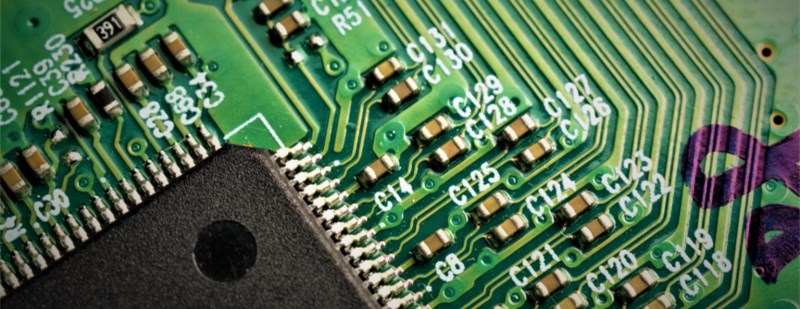
这个电子元件日企拟涨价近3成 手机也跟着涨?
-

这片子观众少到没评分,却看透日本如何培养队长小翼
-

“中国女婿”来救场
-

我们又是冠军,我们总是冠军!
快讯 -
Copyright ? 2018 观察者 All rights reserved。
沪ICP备10213822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220170001 违法及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21-62376571
![]() 沪公网安备 31010502000027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502000027号
![]() 中国互联网举报中心
中国互联网举报中心
 上海市互联网违法与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上海市互联网违法与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